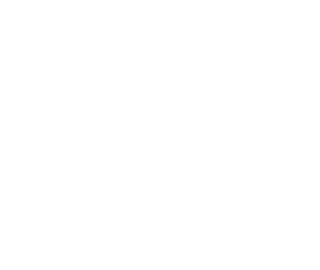龚珏眉: 这从来就不是一个关于自我发掘的故事
拿到NYU Tisch offer的同一天,经历了最失魂落魄的夜晚。丢了手机三个小时打不到车,失联,凌晨坐在环贸门口突然觉得哭笑不得,看着身边的人脱口而出:“你说我们一个学电影一个学时装,这样露宿街头会不会是我们的未来?”
当然,这都是题外话了。
把垃圾摇滚垮掉的一代麦田的守望者和猜火车奉为信仰,却又不得不承认自己更多时候充满软弱不安,我想更多时候比起Dean Moriarty,Sal Paradise才是我的角色:房间角落里唯一清醒的看客和记录者。但对我来说这些精神领袖们的共同点大概是活得真实,所以我也紧跟步伐做着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视利益为粪土,视情商可有可无。代价无非就是不善交际,标化不够。
当然,这样的我,当时也视留学中介为浪费钱。
去年五月我夏校美签面试,我妈在附近咖啡店和另一个同样在等孩子面试的妈妈攀谈起来。巧合的是,对方孩子也是去夏校并也打算学电影。一来二去加了微信对方推荐了我妈让我一定要去树英看看,于是乎我也就抱着试试的心态在夏校期间和DTR电话面了个试,成为了树英2017届最后一个学生。不得不说这么奇妙的经历大概也是缘分。记得当时DTR问我觉得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说是原则。身边不乏SAT考试买答案造假活动的人,但失去什么都不能失去原则和底线。他对我观点的赞同也让我一下子选定了树英,毕竟三观一致实在太重要。
DTR对我一直是宽容的,即使在我扔出一堆借口拖着文书的时候,当然他对我的自信也有时候让我实在是疑惑,至今也没弄懂,但这种自信也变成了我申请季最大最大的精神支撑。EA前的那几个月的确是地狱,每天都在彩排Hamlet试图忘记自己来塑造角色,却每天还要写文书挖掘自己,很矛盾。我理解自己经历的一切造就了现在的我,但我还是抗拒去阐述那些经历的,一方面我更在乎事实而不是背后的原因,另一方面是很多经历没法坦白。
第一稿的long essay我花了七百字拒绝给自己唱摇滚找理由,因为我觉得根本没有理由,就像戈达尔说自己在镜头里放个花瓶一样,他喜欢他就放了,我也一样,我喜欢我就唱了这么多年。虽然这篇愤世嫉俗的初稿被退了回来,但也让我在修改交流时候认识了李佩育,她有时候看我比我自己看得还透彻,倪琰亮也是,在这一年里我们两个一共见过一个礼拜的人居然可以像异地恋般几乎天天聊天。这大概也是树英最独特最温暖的一点,在这里遇到的交心的人,可能比我高中三年遇到的都要多。
这从来就不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故事,更不是关于自我发掘,我一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为此努力。即使学电影几乎是高二一个突然的想法,但就像Yale的教授对我说的,your urges mean something。我很庆幸自己抓住了这个想法,并落实了,因为我知道不做我会后悔。就像在路上里说的那样,“所以我一方面努力把生活过的尽可能任性而自由,另一方面又始终希望可以寻找到一个生命的浮标而永远不离不弃。” 总而言之,我很清楚我是要为自己活,最大的愿望是所有人都可以为自己活。
很感谢我的文书mentor Stephanie,不厌其烦地从我无比情绪化的文书里帮我寻找最合理的表达方式,感谢Bill,在ddl最后关头帮我改了我NYU cinema studies的论文,感谢楚爽老师,不断帮不想找理由的我找到自己的理由。
回到那个失魂落魄的夜晚,满脑子都是Patti Smith和Robert Mapplethorpe在纽约摸爬滚打的经历:身上的钱只够在吃饭和看画展里二选一,甚至都买不起两张票只能轮流去看。我问自己是否有勇气走这么冒险的路,一下子感觉到了全所未有的迷茫。但迷茫有什么可怕的,带着迷茫走下去就是了,我可能看不清未来,但我看得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