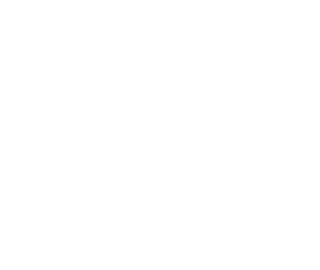树英成长2017 | 撞在这个不言而喻都变成言而不喻的世纪上
看过了许多小伙伴们以及学长学姐的树英成长,开头总是一段鲜活的场景描述。有人从各种角度勾勒等offer时的焦灼心情,有人笔下嗟叹一声“去也”,怀念已过去的申请季。我见过许多次他人笔下初见树英时的绿植,许多次试图从字里行间拼凑一个人的兴趣与爱好,许多次在心里感叹,多好啊,有这样的梦想。抱着同样“别人从我的文字里认识我”的想法,我在落笔的时候总会想得格外的多。上一刻我在琢磨是不是开头的排比用太多,落入俗套,这一刻我又在纠结这儿的标点符号怎么零零碎碎的。老板曾经在催我稿子的时候恨铁不成钢,背地里和我妈说我是个“完美主义者”。我以前很不赞同,现在有点不赞同,因为我爱磨洋工,但不爱完美。这其中的微妙是旁人很难体味的,我总想着和人争辩,但在脑海里演练多次又觉得自己是个孤独的灵魂(呸!),十倍的话浓缩成“唉,算是吧”。就像高明和暴力的代码的区别,输出同样的结果,前者可以占很少的内存来完成,后者要开好多新列表来存放。我不高明,所以我是想得多主义者。
这样说来,比起电脑前或者书桌旁,浴室可能才是我的主场。蒸汽升腾的笔法没有文字的载体,除了引吭高歌便只能天马行空了。枕头上同理,入梦之前盯着天花板还能做些什么呢?UChicago有个prompt,叫你描述一个portal(这时候我又在思考中英夹杂的合理程度了),但不要着墨在它通往的那个世界上。我对着水汽氤氲的镜子冒出这个想法,我的浴室就是我的兔子洞吧,这种奇妙轮回的感觉又是我拙劣的语言无法描述的。中秋节的时候,我带着母上的手作月饼去找Daniel讨论这篇文章。我语无伦次地讲完了我的想法,Daniel很有大师风范地沉吟片刻,拿起了放在桌上的月饼问我,看着它能想到什么。诸君,你们不妨在此刻也停下来想象一下色泽金黄、印着莲花花纹的粤式月饼。当时我是一脸问号的,勉强挤出几个阖家团圆、文化传承的关键词。Daniel和我提到了一本法国作家的小说,大概说的是,主人公吃着小饼干和友人闲谈,突然思绪飘回某年某月的历史长河,遂成为在另一世界的幻想故事。我喜用浪漫主义的比喻,但在法式小饼干和穿越历史中我仍然很难拼凑出一个具体的共性,晓得了这种看似没有逻辑的联想才是新意的所在。后来我在淋浴的时候就想着那个月饼,想到咸蛋黄,想到鸭子,想到农庄,想到乔治奥威尔。“所以月饼是通往反乌托邦的传送门呀。”我在那天的动态里如是说。这个大跳跃之间的逻辑被隐藏的时候,一种很浪漫主义的联想就冒了尖。作为想得多主义者,这非常符合我日常的生活状态,所以我又在心里拊掌大笑,赞美文学的妙处。
不过说实话,那时候笑得多开心,写essay就有多痛苦。我曾经很矫情地和别人说,我有着诗人的脑子,脑海里是星罗棋布的意象和想法,杂乱无章;我渴望秩序,但又害怕失去无处安放的灵感和诗意。现在想想这话虽然很中二,但的确是很能反映如我这样一群人的状态的。对面的人同我讲,大学的教育就是教你如何在这些星星之前搭起桥梁,把它们穿到一起去。这一句话我至今仍觉得很妙(懒得分析,就当做是言语无法描述吧),所以对未来抱有更多的期待。然而,当“满船清梦压星河”落在纸上,就格外痛苦。第一次给我的mentor Jason发essay,他便回了我三四篇分析essay结构的范文,把我完成初稿的沾沾自喜镇压了。和Sarah约了Mock Interview,在她故作严厉的目光下溃不成军,在她指出我语言组织逻辑不足的时候,把“逻辑清楚”说是个人优点之一的我感觉脸上火辣辣的疼。完全推翻Long Essay的初稿构思和文字,去找Jade谈人生的时候哭得昏天黑地,老板一脸无可奈何地说“要加油啊,要写啊,有我们啊”。我对文字的爱在我心中用沙砖搭起了一个巨人,看似无所不摧,实则无所不摧,都是虚的。修修改改背后的挣扎凝在这里,又与何人说?我觉得树英成长,落在成长上面,也不全是一颗种子长成大树的过程。木秀于林,哪片叶子不是新的?我的成长便是在一划一画、一言一语中堆积起来的。
申请季前最后一个暑假,我去ELAC夏令营体验文理学院的学术生活。Cross Cultural Awareness课上大家朗读自己的体现个人认同的诗作,了解不同的文化刻板印象并学会包容。课后我找Karlene谈年龄歧视,这位黑人女教授微笑着和我说,这很难,但我们要去改变它。我和室友Ying在摇滚和舞曲中手舞足蹈,在发现共同爱好的时候惊喜地大叫,把助教Isabel拖在房间里畅谈(安利)中国文化与西方的异同。小时候我说要做老师,后来想学心理学、学中国史、学文学,长得越大知道的越多,就越对自己真正兴趣所在感到迷茫。我不擅长理工科,但总有些人嚷嚷着我们必须向现实低头。我欣赏社科但不热爱在数据分析与人性的夹缝里生存。我坚持对美的追求,但学纯文学实在是太理想主义的事情了。初读罗素的“个人陈述”What I Lived For便深以为然——我同时憧憬着理性与感性,这大概也是我选择文理学院的主要原因。灯影下的都是未知,我愿意探索。
在我心里,申请季的特殊性不在于任何别的,仅仅是这段时间联想性的出奇丰富,比如看到生活中一个小细节就能扩展成一篇文章的构思。写下这篇文章,算是一个放飞自我的个人陈述,剥开文字便是摆脱了条条框框之后的我。(作为想得多主义者,我一直在思考我不分小标题的叙述会不会让后续的排版感到困惑。)尤其感谢所有过去申请季认识的你们,没有由于我的年龄而对我这个00后式幼稚的指责或者特殊优待。除了所有在现实中伸出手帮助过我的人,我要感谢一群隔着网络无声地陪伴我、鼓励我,在不知不觉中改变我的可爱的人。我不爱说很多这样的话,又怕诸君觉得我是个不有趣且不识趣的人,便引了木心先生的一首俳句当做标题,希望大家能明白我的“不言而喻”。
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