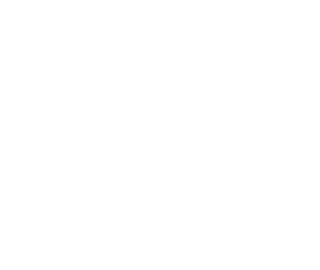树英成长(研究生)2018 | 在光中看见光
在光中看见光
这是一篇拖了三年的树英成长,其中几经提笔又放下。对我而言文字构建的世界,通常依托于某一个特定的主题而展开,纯粹而又美好。可是真实世界并没有既定的法则,寻找的道路上,也不是一路充满了鲜花与凯歌。所幸这三年,角色的转换与所处的位置,都和树英若有若无有着某种默契的关系。于是也让我有了更丰富的视角,去思考留学和申请这件事情。我把三年中的经历与记录杂糅在一起,以期用时间顺序的方式,去记叙一些思考与成长。 第一次认识DTR缘于一篇关于他的人物专访。那时候我念大三,在中国第一个创新人群故事传播平台—中国三明治(China30s)实习。在设计中信出版社合作书籍,《30岁后,为梦想寻找现实的出口》的人物内页时,见到了这位传说中高“暖”的大男孩。
正如DTR所说“大学生相比高中生,思维往往有些僵化且现实”,他喜欢有梦想的人和愿意为梦想付出行动的人。当时的我身边充斥了太多的机会和意见,对于是否要出国念书这件事有一些顾虑。往往飘忽的状况下,需要的只是一个肯定的声音,于是我决定去树英找他聊天。
在我“权衡”与“抗争”的过程中,DTR从一位老师变成了一个朋友,即使我几乎放弃了出国的念头,他还是他,支持我的每一个决定。他特有的乐观和积极也一直陪伴着我。
大三上学期,我刚结束在TEDxYouth的演讲,收到了迪士尼乐园幻想工程团队的面试通知。我很清楚地记得DTR回复我说 “啊啊啊啊~太!好!了!快来树英老板帮你mock interview!” 他就是这么单纯又善良的人,抛开那些所谓的名校光环,更重要的是他在意你的成长,也尊重你的人生。 2016年夏天,我从同济毕业,毕业论文获得国际金奖,同时被罗德岛设计学院录取。拿到录取信的后几天,照着树英人的惯例写了一篇树英成长。题目是《Be with DTR》。为了激励自己,在我电脑里有个文件夹就叫这个名字。那也算是我给自己打气的一种暗示,心里想着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进了自己想去的学校,应该写篇文章聊一聊这个文件夹给我带来的力量。不过那年,我被教授说服,留在了上海的建筑事务所工作,这篇文章也随之悄悄“冷藏”。
工作的那段时间好像满足了我对亦舒小说里白领生活的幻想。相比于在象牙塔里做一个高绩点的好学生,我更喜欢不同情景交织在一起的层次感,也喜欢项目落地带来的满足感。将近一年中,从室内建筑到综合体的规划,大约接触了七八个项目。我很享受在香格里拉主持完地产开发的会议,就穿着小高跟鞋跑去工地和工人讨论结构。也愿意接受临时取消行程,在酒店里建模,像打仗一般,隔天又拎着旅行箱飞去和甲方汇报。加班和熬夜并没有影响我对设计的喜欢,反而对这件事多了一份尊重。我是一个想做事情的人,对留学没有特别什么执念,只是家人的坚持,让我只好在工作之余的点滴时间中重新整理思路,进行了第二次申请。三月的一个晚上,我照例查看邮件,妈妈一边看电视一边安慰我说:没关系,如果被拒绝了你还有工作。我和她说,“妈妈,我好像被哥大录取了”。那天,爸爸在外地,喝了点小酒很早就睡着了。妈妈跑进我房间,我们两个人并排躺着,也不说话。过了一会她说“让我们想象水流过身体”,她说这样的练习可以帮助睡眠,但是其实我们都失眠了。这一幕我一直记得清楚,后来几乎再也没有和妈妈顶过嘴。
去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前,我还是忍不住又接了一个项目,去海南出差,参与一个海岛开发的投标准备。飞机上又写了新一版的树英成长,题目叫《在光中看见光》 …… 白先勇在《纽约客》里描述了一个情景,黄凤仪在给母亲的信里说:“带着太阳眼镜在Times Square的人潮中,让人家推着走的时候,抬起头看见那些摩天大厦,一排排在往后退,我觉得自己只有一点丁儿那么大了。淹没在这个成千万人的大城中,我觉得得到了真正的自由:一种独来独往,无人理会的自由。” 到了纽约之后我发现,这座城市吞噬着个人的悲伤和故事,它的热闹就像是盛大的游行,你可以选择加入或退出,但是那种热闹是自顾自的,不会为谁停留。我像一个刚学会说话的小孩,接受着全新的信息。只是我喜欢这样无依无靠的陌生感,它飞速的更新和迭代,不得不把你打回出厂设置,同时你也有机会可以有重新选择增加或删除性格(characteristic)的机会。我又悄悄放下了树英成长:如果自己不能消解不适,不能内心挺拔,我怎么希望文字能带给别人正向的力量?
纽约可以说是学习建筑与城市设计最好的实验室之一。 从康尼岛(coney island)上的游乐场到华尔街交易所里里闪烁的数字,它如同《Delirious New York》中描述的那块“被扔进烤箱的蛋糕”,最初烘焙者只是无心地在上面放了一个没有经过太多考虑的方格网状的铁架,但欲望和资本像温度一样渐渐升高的时候,曼哈顿的表面也随之膨胀起来——从铁架的空格中——直到变成一大堆伸长了脖子争抢阳光和空气的针。” 这是一场关于人类意志与幻想的梦中之梦,在细节与幻境的层层堆砌下,验证其自身的的荒诞与真实。生活在纽约的人们,都有着某种特殊的共性,他们同时兼有“曼哈顿实验”参与者与试验品的角色。通过日复一日的“造梦”与“打破”,去实现自己对都市生活的幻想。不同于传统教育系统下的建筑或规划学科,哥大的教授们更关注将城市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转换设计的角色和视野,重新定义二十一世纪的都市景观。通过重新整合和缝合公共空间,社会正义以及生态系统之间的联系,从而提升城市对于一系列变化的弹性与适应性。在这里的学习中,我们不断地追问一个最基本却又不可忽视的问题:什么才是一个“好的城市”? 在这里,如果个人失去了对生活的控制,只能努力反过来控制自己。我希望自己可以专注设计和简单的生活。除去studio本身繁冗的讨论与漫长的电脑绘图外,尽可能多的呆在图书馆做阅读,尽可能多的去听各种学校里的讲座,尽可能多的去writing center找mentor练习英文写作。除此之外,把家里打扫干净,给自己做饭,练琴与运动。 那一段时间,是飞快的,但也是静止的。我像是一个性格被抽离掉的塑料袋,塑料袋容易被吹走和忽视,但是可以装下很多东西。 慢慢的,我的眼睛里出现了想要看到的自己,于是生活渐渐也变成了我喜欢的样子。我一直在努力等待这个不违背,等待这个从心而发,正心诚意的涌现,基于自尊,也是尊重。
加巴蒂斯塔•维柯说过:既然人组成了这个世界的国度,那么,理应在他们的心灵之中寻找世界的法则。生活中可以追求宁静致远,向内而求的力量。同时,也需要一些打着鸡血的仪式感。
“大德敦化,小德川流。道并行而不悖,同途而殊归。”看似嬉笑怒骂间,好的成绩不经意就涌现了出来。但其实率性背后,树英一直在用心为学生们建造一个小时代,每一个细节都被精心设计好了,放在一体,它不仅仅在意一个人拿到了多少张offer,它似乎还想给你看更多的生活方式,关乎成长,关乎个人。这就是我对DTR和树英的理解:光芒背后,有被我们忽略的感性与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