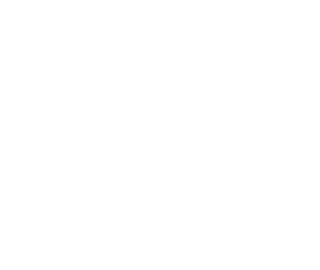树英成长2018 | 我和我的树英三年
我和我的树英三年
初三毕业确定要出国后,暑假老妈帮我找到树英做我第一个学托福的机构,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模考TPO11,阅读19、听力17。我从小就不是一个英语好的学生,当时拿到这个成绩还十分激动。记得佳易姐在欧江19楼的图书馆里和我聊了很久,建议我上托福的强化班。那个下午,我和我妈在徐家汇公园逛了40分钟,一直在纠结是安稳地上树英基础班还是挑战下强化班,一天600个单词背诵量让我恐惧,却又诱惑着我,鼓励我在15天里跨出一大步。我妈说那是她记忆里我最用功的15天,除了吃饭睡觉之外,所有活动只有背单词,做练习,很像我现在身边正在准备高考的体制内同学们。我当时选择了强化班。
那15天里学到的不止是应试,更多的是学习思维上的转变:从初中单纯的死记硬背变成开放性思维,有边界但没有束缚,可以在准许范围内做一切想做的。在高二时每个周末都会跨半个上海去树英,因为在那里会有志同道合的朋友聊天,会有老师解答题目,有时还会有催weekly report的元元和偷吃外卖的DTR。这些缺一不可的构成了我眼中温馨与自由的树英。我还在托福班里见到了幼儿园、小学、初中同学。
那15天代表的也是树英一直给我的印象,那个印象始于三年前也永远会一直留在心底,那个在这里我们可以去尝试一切,而树英则会提供你想要的所有支持。树英带着我做了OWE Rock 摇滚演唱会,参加了树英T-shirt设计创业大赛,还领着我去美国参加树英之夏看未来的大学。比起我身边很多同学口中听到的他们签约的中介什么建完全不存在的社团,帮忙乱编活动、买获奖证书、代写essay,我始终觉得我是那个做了正确决定的人。尽管在签约前没和其他中介比较过,但树英是真实的,是带领着我们去经历与探索的。这种真实,就像曾经那个害羞的我在OWE舞台上第一次上台表演架子鼓一样让人值得回味和纪念。
时间很快走到了申请季的文书班,如果说3年前那个15天的托福班是苦的话,高二的那15天的essay班应该可以用非常非常苦来形容了。记得每天从早到晚地寻找脑海中回归自己的人生靠着点点的记忆用来写long essay去回答那个关于“我是谁”的终极问题。那段日子我时常记得夜里经常写到一半被迫放弃重找灵感,那种灵魂的拷问似乎也让我在那段时间里慢慢了解了我想去那和我为什么来。之后why major和why school接踵而来,摧残着我的大脑和身体。但是在那段时间里,我印象最深的却不是一次次失败的文章,而是每天下午四五个人关在房间里,互相交换着自己不算长的人生中发生的形色故事,有的听了让人大笑,也有的伴随着眼泪。这是我记忆中十八年来我第一次说出自己的内心,也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别人的内心,也让别人靠近我的内心。我终于在essay班倒数第二天的时候定下我大学申请的long essay主题。
不停的更新Common App、和我的文书mentor Stephaine来回修改essay、纠结要申请的大学成了我essay班之后的主旋律。Again,不像我身边同学的其他中介多申一所需要补交费用,树英在学校选择上没有限制,在老板口中只要我们能能有质量的写完自己的申请文书,想申多少都可以。于是乎那个秋天的每个周末树英成了根据地,我力所能及地征求着每个老师的文书修改意见,选择适合我的学校,和Sarah坐在沙发上开着玩笑的同时顺便改一下午的essay,再一起订杯奶茶。
11月1号前的那个周末,我在陪了我三年的DTR面前仪式感地提交了我的ED1学校NYU的申请。老板说,来个永恒的回忆吧。
好了,我想该收尾来了。从初三结束第一次步入树英到现在高三快结束马上从这里毕业,三年了,这个地方变了很多,从原来徐汇欧江大厦搬到了黄浦SOHO丽园,从原来的两层楼变成了现在完整的大平层,但是不变的却是我的文字功底还是一样的不好。写到现在也好像也没有像其他小伙伴一样体现出自己的成长,反而更像是在写关于记忆里的随笔,想到什么便记下什么,还有很多已经记不起来了。但这些都是我对于树英的理解与记忆,是我想要展现的。幸运的,我和最好的朋友们一起进了NYU。
看到这里作为读者的你应该想说这篇也太无聊了吧。不是你的问题,只是真的因为作者是一个文笔很差的人,因为这篇”文章“里没有“层层深入”,没有“主旨升华”,倒是可能有很多用错了的标点符号。但我希望在读完这篇关于树英的故事后,你自己也能找到属于你的。
嗯,故事的最后,我最近准备去好久没去过的树英再和你们喝一回长久没喝的下午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