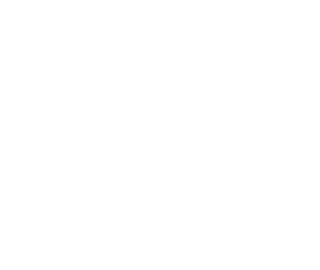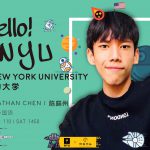树英成长2018 | 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开始动笔时,距离收到offer的那个瞬间已经一月有余,各种心境确实有过无可比拟的惊喜,但更多的则是一种迷茫、惶恐和不安。因此对于申请过程,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再敢去回顾,更没有勇气做更多的分享。现在重新捧起了一些为了单纯的愉悦而去读的书,再次开始做只需要一个想法就能迸发全部激情的课题,我想我也许找回了一些东西,一些适合写在这里,关于三年的文字。
想到高中的时候,我会带着垮掉的一代那种浪漫又悲观的眼光进行审视,将那些模糊的记忆变成场景式的静止画面。在这些画面里,我很喜欢去年冬天,在蒙蒙雾霭中被空调吹的过度温暖的寝室。623的深夜代表着刷题、读书、故事会和夜宵,以及对于未来的无限憧憬和用不完的精力。我们想尽一切办法不睡觉或是到什么别的地方工作,而这种生活对我来说有那么一点康德绝对律令的意味,我的义务,我的自由选择。也是那个冬天,我会想起白炽灯下恍如隔世的实验楼,被我消耗的白纸和看不懂的论文。在此之前我从没有想过做研究,现在我想不出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让我感到快乐。当然,还有那个被我带着骄傲的语气讲述的为什么要学CS的故事:一半是情怀,一半是接受。其实仔细想想,这样的决定真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某种程度上来说和我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设偏差的太大了。不过我很感激在这一件事上无条件地给予我信心和支持的人,这其中包括在我学coding之前就和我谈着高维数据和可视化的一个朋友,以及在耶鲁请我吃了饭的程序员小哥哥。这段岁月,步履不停,在薄雾的晨钟里看到光芒。
王小波说,似水流年是一个人所有的一切,只有这个东西,才真正归你所有。作为一个躺在河底的人,我显然不应该尝试伸手去抓住波光粼粼中漂流而过的落叶和浮木,而是就那样在似水流年中感受一些更内敛的东西。所以话说回来,拿到offer那一刻的惊喜不久就被变为生活的序幕,只是偶尔想到我真的是UChicago的学生的时候,会感叹一下命运的奇妙。更多的,我在反思申请季的自己。
ED截止日期前二十天,我删掉了最新写的一稿UChicago补充文书。那天晚上,我在操场上走了一圈又一圈,在初秋的晚风里躺在塑胶跑道上,看着黑夜思考,我该怎么办。一阵恐惧在那个瞬间击中了我,我近乎绝望的意识到,在这半年里,申请成了我生活的全部意义。然后呢?那考上大学以后怎么办呢?从小到大的精英教育让我们身处在社会的某一个盲点,向上是迷雾重重的高处,向下是不曾着眼的市井。从某一个时刻起,有一个楼梯已经为我搭建好,我在无意识中一步一步向上攀登。一边呼喊着为民生为社稷的口号,一边又是常春藤的绵羊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把某期《十三邀》反复看了无数遍,在那之中听到公共知识分子对着假想的听众泛泛而谈,追求精英化的大众文化,而真正组成这个社会的个体却在被遗忘中继续着自己的生活。于是,再想起无数鲜明画面重叠的,富有生命力的过去的时候,我想起一个我真正觉得“important but under-discussed”的话题。
后来,这篇文书成了我能写出的最“我”和最“芝加哥”的东西。当然这其中仍有无数亟待解决的自相矛盾之处。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之间的界限依旧模糊不清,文字间也带着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强赋新词之嫌。不能在写作时知道这篇文章究竟该归于何方,有何作用,或许是我的一大遗憾。幸运的是,芝加哥的AO认可了我的这一点想法。
当然,可以在芝加哥凭自己的兴趣读一些有趣的书,是我自美国回到上海后就开始向往着的。不过,我还是申请了Gap Year,想要将这种期待再默默地放在心里一年。其实申请的时候并没有想那么多,无非是想趁着这一年安静下来,寻找某种内心的执着,追求某个事业。缘起很简单,是申请前的六月份我在微博上发的一句话,申请后想要回到祖父母的家乡,多花一些时间陪伴他们,也趁机会了解当地现状。那种陪伴并非出于愧疚,而是一种我想象中生活应有的走向。之后我逐渐想清楚的是,间隔年(Gap Year)不该是用来弥补过往生活中失去的什么,相反,此刻所做的事情会加在一起,成为我为间隔年做的所有准备。说这是一个随便的决定,我也并不否认;不过,柯希莫一开始在树上生活的时候,应当也是很随便的(笑)。也许我会旅行,也许会见到一些目前生活圈之外的友人,寻找一些抽象的,但始终美好的感觉。送给自己,也送给所有正在迷茫期的朋友们一段话,来自音乐人程璧:
走过寂寞的小路
穿越过无人的荒漠
疾驰在湍急的河流
漂泊在无边的海
细数过往俯首之间
都可看到天空之远
愿你。
——《步履不停》
洋洋洒洒的写了很多自己的感觉,现在该是要感谢一些身边的人了。
爸爸妈妈一直在包容我的焦虑、烦躁和任性,让一部分的我能够在野蛮生长中获得一个还不错的结果。从选择出国开始,就开始一个人走在前面,自己做着决定,什么也不说,让他们不断的担心。从一开始的非文理学院不申,让他们做了近一年的心理准备,后来又跑到芝加哥这么一个冰天雪地的地方,买鹅还要花一笔钱。谢谢爸妈啦,真的。希望未来能让他们少一些担心,做一个成年人了。
还要感谢我的SAT语法老师徐颖,也是树英很多小伙伴的老师。阿姨是我见过最好的语法老师(虽然我也只见过她一个)。在她的工作室里,有吃不完的零食和刷不完的题,带考团也是一次不会后悔的拔草之旅。她永远是最后一个走,也永远以最快的速度回微信答题。就是这么爱她。
再来是关于—–我的树英 ❤️。
如果要说第一次和老板接触,那是一年前这个时候的一次电话。我问Pace佩育学姐要了老板的微信,他说明天就要去美国,所以干脆打个电话好了。于是我一边给他发了我的过往经历,一边在电话上向他描述了想学的专业和想去的学校。那通电话之后我和老板几乎同时给Pace发了“对方也太棒了吧”的消息,被学姐吐槽“你们真的是两情相悦啊”。后来我在因为SAT2过度焦虑的五月和老板在安福路的餐厅聊天,并因为那个契机成了2018届第一个遇到Kerri的人。再到美国时我和妈妈在老板女儿未来的母校Barnard College与老板“偶遇”,当天恰好是老板生日,特意去他母校Columbia买了明信片写给他。年底的时候老板去了美国,就和大姐接触的很多。其实今天能获得这个结果,是真的最应该感谢大姐的。记得夏日将尽的那天,欧江大厦几乎被搬空,本也不是大姐的工作日,她却是推着婴儿车带着佑佑来和我聊天。一边听着我讲package,讲对未来的想法,讲对当时REA这个想法的不确定,她突然说,“ED芝加哥吧”。后来你们都知道啦,我改了ED学校,慢慢实现着一个很“我”的决定。还有颖杰老师、璐璐姐和007老师,你们都是树英的灵魂所在。
接下来要说我最棒的文书mentor Kerri和Jaime。我的主文书整整换了三个主题,改了16稿,最后一稿是在交完ED后才finalize的,没用上着实遗憾。七月初的Essay班开始,我总想要避开一个我觉得“没有感情”的话题;后来我想要一个完美的类比,用隐喻穿插起主文书每一处的思想,却始终写不出那个真实的自己。十月份写到焦头烂额的时候,Kerri不断地安慰我,耐心地在微信上和我brainstorm,在截止日期前我交了一篇一千多字的稿子,Kerri一夜之间把它删到了650字。我的overseas mentor Jaime也是一样敬业。因为时差,她特意一早起来和我skype讨论补充文书。我在Wellesley Early Evaluation 截止当天收到了她给我的一篇几乎final的文书大大小小的意见,一下心急如焚,问Jaime能不能等我很快把改好的发给她,她就真的推迟了自己的睡眠时间帮我改文章。在过去的申请季我能写出那样personal又真实属于我的文字交给大学,是要归功于她们的。
还有我在树英遇见的那些小伙伴们。Essay班被我缠着改文书的peer mentor Max,超级温柔的Hanwen,还有被我拉着做mock interview的Joseph和Stella,都在这个过程中帮了我太多。Stella读到我第一篇主文书的时候说,“你真的很适合芝加哥诶”,让我再次对本来已经要放弃的UChicago燃起了希望。出ED结果前一天我给Hanwen发微信说好紧张,第二天一边读到congratulations一边激动着回复她。还有Pace,虽然没怎么见面,但却语音聊了很多次,不仅关于申请,关于专业,更关于一种人生哲学和同类人之间的交往。树英2018届有好多有梦想的小伙伴们,像刚来树英时就被老板拉群说“我觉得你们会成为很好的朋友”的雨桐(非常为她开心),在香港一起复习一起缅怀过去的居瑶佳等等。和他们的接触会让生命充满积极的光,潜移默化中从正面影响着自己。最后呢,要特别感谢认识七年,现在在莱斯大学的郑睿。距离第一次从他的朋友圈知道树英,也过了近两年了。申请季的时候无奈地和他说我写不出文书,他就打来语音,并不谈文书,而谈一些身份认同和关于未来年轻人都有的无措,让我深受启发,也深感自己的无知和短浅。显然,我并没从他这里收获什么鸡汤式的格言,大部分时候也在不友好地套路他,不过,谢谢啦。
这是一篇没什么主题的树英成长,很感谢看到这里的你。我仍在路上,并未停止自己的脚步。杰克•凯鲁亚克在《达摩流浪者》和《在路上》里描写的生活始终令我心向往之,带着某种不可终日的惶恐和微妙的期待,“我们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