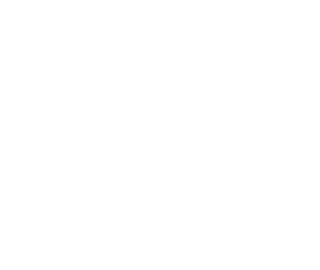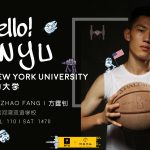树英成长2018 | 唯有自己不可辜负
唯有自己不可辜负
- “痛苦来自外界评价与自我认知之间突然出现的巨大反差,整个世界呈现出一种令人不安的陌生感。”
从小到大,我对于学习,都抱着一种”不思进取“的态度,属于那种能刚刚好过线就绝不拿满分的类型。大把时间花在了旅游,读书,发呆,和天马行空地想象。按照我小学班主任的说法,“花加倍的时间只为了把成绩从93分提到100分都是不值得的”。在平和读了8年的我,远离强压,远离补习,远离竞争,像是个不知人间疾苦的贵公子,抱着我那一亩三分地,自我满足。一直到初二下半学期,学校在四月初的家长会上宣布改变方针,要求所有学生参加中考。为了躲避中考的填鸭式刷题大法,我妈决定送我去美国读高中。就这么匆匆忙忙在一个月内完成了申请步骤,并在五月一号截止日当天晚上才递交了唯一一份美高申请。
意料之中的,我被录取了。九年级的课程比较简单,学术上我几乎是无缝对接地继续着“低空飞行”的学习模式。兴许是我妈再也看不下去我散漫的“放羊”模式,准备给我收收骨头,又或是她耳根子软被周围的ABC推妈们成功注射了强效鸡血针,反正她是焦虑症发作,态度决然地拒绝了原来高中提供的各项honor program,义无返顾地带着我转到了当地的一所学术声誉颇佳的蓝带学校。然而,当时对于美高学习没有任何了解的我,根本不知道转校会对我的课程选择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所蓝带学校对于转学生的政策很严苛,很多credit并不承认,所以原本可以选修honor课的我被降到了普通班,数学更是连降两级回到Geomertry。作为当地类似USC与UCLA的体育竞赛对手,新学校与老学校校风大相径庭,怎样融入新学校的氛围也成为了一大难题。
在普通班上百无聊赖地听着毫无挑战性的课程,回到家再听到我妈说着别人家孩子的各种鸡血故事,我第一次感觉自己成为了一个失意的loser,每天浑浑噩噩。自我认知与外界评价之间突然产生了巨大反差,世界在我面前崩塌,留下来的,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失重感。那时的我,仿佛在黑暗的通道里爬行,摸索着,看不到前进的方向。我开始怀疑自己,怀疑自己所作出的决定,甚至怀疑自己的能力。可笑的是,人处在绝境的时候会全然忘记曾经的意气风发。我开始怀疑自己的坚持是否仍旧具有意义,这样碌碌无为的生活是否值得继续下去。
“呀,你怎么还在上Geometry?”听着老同学不无可惜的语调,我的心沉入了低谷。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是承认我的选择错误?或是抱怨学校的不公?
学习上向来顺风顺水的我第一次陷入了迷茫…我的自信与自我彻底被摧毁。
“如果在这所学校学习,让你这么不快乐,那我们就转回原来的学校吧。”整出这场幺蛾子的我妈,又来试图力挽狂澜(挑起事端)。
老学校的顾问热情地接纳了我, 并承诺给我全honor,附加1门AP的课程。欣喜若狂的我仿佛抓住一根救命稻草,当下决定转回原来的学校。却不料到,办好转学的手续之后,我再一次与顾问沟通的时候,得到的却是与之前截然不一致的回答。开学2个星期,honor与AP的老师大多不愿意从头开始教转学生,实验室的课程人也已经满员,无法接纳新的学生。这对我来说是再一次打击,调整完的课程难度甚至要比之前转学后更简单。又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但已经没有可能再改变了,我只能选择接受。转学后也不轻松,老师要求我将之前落下两个星期的作业考试全部补上。关键时刻,身体掉链子,我大病一场,又是三个星期没去学校。To Do List上满满的事项就像巨石般压在我的心头。
那段时间的心情很焦灼。其实害怕的并不是无法补齐作业,把GPA拉上来,而是担心这段经历将成为我简历上浓重的一笔污点,我无法再向之前计划的那样一阶阶台阶一步步往上走。私立学校的课程一环紧扣一环,没有先前的铺垫,之后就没有办法选上有难度的课程。
生病在家的时候,身体昏昏沉沉,脑袋倒是越发清醒起来。小时候对于“人生很长”,又或是“失败乃成功之母”之类的鸡汤名句总是嗤之以鼻,可是直到我经历了失败,才真正理解了这些话的含义。我知道这很cliché,但是,在那次经历中,我学会的是如何跟自己和解。如何学会容忍自己的失败,接受它,并接纳它成为自己的一部分。那时的我,如果没有接受现状,或许就真的破罐子破摔,就此沉沦。庆幸我从小也就是个随遇而安的性子,学习也向来不算我人生的头等大事。虽然我妈总以“怒其不争”的口吻怼我,但不可否认,也就是我常年来这“不求上进”的心态让我可以很快接受现状。毕竟再反省自责曾经轻率转学的举动已无济于事,摊在手边要做的事这么多,还不如一件一件慢慢来。
“其实哪有什么女汉子,不过是一个个把眼泪变成了盔甲的女孩。”
我收起懒散的性子,时间大多花在提升自己各项技能之上。这让我摒弃了许多周遭的声音—谁家的孩子又拿了竞赛大奖;谁家的孩子这一年GPA又高达4.8—我以一种从未有过的谦逊姿态来面对学习,不给自己定下过于远大的理想,而是专注于当下,完善自我。
回望那段时光,才意识到,是它,犹如当头一棒,唤醒多年走失于迷雾之中的我,像是一缕阳光照进我那黑暗尘封的小房间。原来追求的”岁月静好”的生活,不过是面对竞争压力的消极怠工,亦是对于自己的不负责任。
现在想来皆是梦一场…
记得读过的一片文章里,讲到阿里集团副总裁王民明对于成长的描述,“成长就是不断地与系统、与客观现实碰撞。在这个过程里会不断地碎掉,然后重建。在每一次重建里,扩大自己的边界,容纳进来更多的真实的东西,就能掌控更多东西。”
而这些经历过碰撞,破碎,后得以重建的人们,往往能在那些黑暗时刻看清更多的东西。
- “真正能走出黑暗并重新启程的人们,都是理想主义者”。
帮助我真正走出自我怀疑的,是我在不断提升能力探寻自己时,所发现的,自己的激情所在。
双鱼座的我,从小爱天马行空地想象,可讽刺的是,我实际上是个极为理性的人。在身边孩子们畅想成为宇航员,科学家,或是记者的童年里,我就是个没有梦想的人。曾经的我为此恐慌,不安,受挫。明明每件事都可以完成得妥妥当当,没有什么缺陷,可却没有什么事能真正激发我的兴趣。
一直到十年级经历了转学风波后,平静下来的我,开始寻找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生物,是的,那个许多人听来就觉得头疼的学科,就是我所谓的“激情所在”。而让我对生物产生浓烈兴趣的就是我十年级的生物老师。一个高高瘦瘦的金发女人,将自己所有的热情投入到这一门生物课。她的生物课从不枯燥无聊。午饭后的第一节课,是摄入碳水化合物,胰岛素大量分泌,导致血糖迅速下降的时刻,用人话来讲,容易犯困。可生物课不会,女老师擅长将各种生物理论应用到实际生活。记得讲解植物pheromone的时候,老师举了个有趣的例子。文艺小说里最爱写的“青草的芳香”实际上却是青草在生命被割草机“抹杀”前最后的呐喊。老师满脸的惊慌,双臂摆动,模仿着青草大喊“Run!”,后又玩笑般地加了句“If you can!”
对于刚刚走出黑暗的我来说,生物就是让我重新启程的所在。我开始有了努力的目标,以及为此奋斗的动力。此后两年针对生物所做的活动更是让我进一步确认了自己对于生物的兴趣。我在夏校学习了各种生物实验室所需的技能,从最简单使用micropipette的技巧到细菌培养,PCR和Gel Eletrophoresis;我在复旦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实习,了解到生物领域最尖端的实验,并激发了我对免疫治疗的强烈兴趣;我进入一家名为大家中医的公司实习,尝试着从生物的角度来理解中医。美高学习的生物课告诉我一切知识来源于实验,而暑假实习所了解的中医理念却颠覆了我一直以来的理解。这些无法用科学解释的现象引起了我的好奇,也同时激起了我的疑问。中医在谷歌上被称为“pseudoscience”,可针灸与拔火罐又是外国人也不得不承认的治病良方。那么现代医学呢?人们依赖的现代医学有没有问题?小孩子从小被教育要经常洗手,殊不知这样杜绝了有害细菌的同时,也让人体丧失了辨别细菌好坏的能力,从而免疫力下降。那么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我们知道如何杀死细菌,可这是正确的吗?
在这之后,我进入了耶鲁的YYGS夏校,遇到了一群像我一样,对周遭的一切保持好奇心的人们。夏校的这段时间很充实,耶鲁按照每个学生的兴趣安排了各种有关生物的课程。Interdisciplinary的课程设计在生物课中融入了物理,化学,文学,哲学,和传媒。每天一大早的几百人的大讲座之后有分组讨论。分到我们组的assistant是耶鲁在读的黑人小哥哥,他不热衷于讨论讲座里的技术性问题,而是希望我们从哲学的角度讨论生物,讨论每项技术背后的ethic和实际运用情况。每天的Seminar让我接触了与生物相关的各种领域,包括我所感兴趣的免疫与基因。Seminar课后还安排4个人一组成立CAPstone Project小组,选择感兴趣的课题,在最后一天完成演讲。我们小组选择的是Alzheimer’s Disease,俗称老年痴呆症,并且研究可行的基因疗法,通过改变基因信息来免除大脑中信息不流通的问题。这段时间的夏校让我系统性地了解了生物专业的各个方面,也认识到了自己的兴趣在于基因,细菌,免疫系统,和生物伦理学。YYGS还让我遇见了一群相见恨晚的朋友,每天晚上,来自八国的女孩在寝室里聊天到半夜,让我这每天十点半必睡觉的人都恨不得眼睛上支个火柴棒熬夜修仙。最后那个离开YYGS的女孩,终于认清了自己的目标,了解了自己想要什么。
“真正能走出黑暗并重新启程的人们,都是理想主义者”。是的,我成为了一个理想主义者。我想,这也没什么不好。我不再对于Why major这个题目束手无策;我可以时刻向人讲述自己对于生物的兴趣;我可以与面试官畅想未来免疫疗法带给癌症病人的希望。
“You are the books you read, the films you watch, the music you listen to, the people you meet, the dreams you have, the conversations you engage in.”
我所经历过的,我所遇见过的,我曾经与之对话过的;让我痛苦的,让我喜悦的,让我好奇的;不论是那些黑暗的时刻,亦或是欢喜的日子。所有的这一切,都成为了我身体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改变,塑造,完善着我的价值观。若是现在问我,当时转学是否是个错误的选择。我恐怕无法回答。转学让我选课失利是事实,可如果没有那样一段经历,我或许永远都没法打破自己给自己的设限。曾经的我,就如心理学家武志红在《巨婴国》中写到的那样,贪恋那一份如母体子宫般自在的原始舒适区,渴望逃离现实。后来的我,寻找到自我的意义,找到为之努力的目标,遇到一群志同道合的好友。而现在的我,带着这样丰盛的自己,正要去拥抱崭新的生活,追求那之中无数的可能性。
- 我所追求的,那无数的可能性
这之后的两年,我奋起直追,GPA犹如神助,像股票般“直线涨停”。ACT,AP课程,SAT II,我是“遇佛杀佛,遇神杀神”。然而转学对我GPA带来的影响,却是不可否认的。ED被拒带给我的,是不被认同的失落感。要形容当时的感受,或许就是“孤立无援”这四个字。为什么会这样?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我这样问着自己。就像个巨婴那样,我渴望被看见,希望别人认同我的努力。再次失去对于未来的掌控感,那是一种沉重的无力感。
又一次与现实的碰撞,又一次碎掉。但这次的我,已经不是两年前那个脆弱的小女孩。
就是在这一段时间,我遇见了DTR。他非常斩钉截铁地告诉我妈,“Celine没问题的。”曾经的我,寻找的是一份继续的意义;这时的我,所需的是一份外界的肯定。肯定我所做出的努力,也肯定我所选择的道路。我非常感谢在那个我最黑暗的时刻DTR当时所表现出的,对我的认可。
都说“治疗失恋的最好方法,不是时间就是新欢”,被女神校拒绝的情伤在收获来自暖男USC的表白信后被彻底治愈了。记得当时,夏校的朋友喜滋滋地来告诉我,他被提前录取还获得了Trustee全奖奖学金的候选人资格。而迷迷糊糊的我过了三天才被我妈催着去看拒信。或许是从没妄想过USC的奖学金,打开admission portal看到状态变为admitted student时我还没反应过来。直到打开录取信,看到Congratulation。那一刻,大脑是一片空白,跟演戏似的关掉页面时手还在微颤。傻乎乎地过了两分钟才想起阅读之后的内容,这才发现录取信的第二页还有一段文字。在Merit Scholarship Status下,是一句Congratulation!You have been selected as a finalist for a full-tuition scholarship。
我为什么最后选择USC?不是气质独特犹如高岭之花的Vassar;不是在生物领域有着尖端造诣的UCLA;亦不是大佬聚集的Berkeley。
作为申请季收获的第一封offer,USC对我的意义是特殊的。我不清楚USC究竟是看重我哪一点,毕竟比起身边收获USC奖学金的学霸ABC们,我成绩单里的B可谓是触目惊心。或许是看重了我一路奋起直追所展现的潜力;或许是我essay中那些稀奇古怪的想法所体现的个性。USC的offer之于我是一份vindication,像是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告诉我:我的努力,有人看见;努力后的成果,有人欣赏。回馈于USC对我的这一份赏识,我也同样相信,在USC,我可以追求我所畅想的未来的各种可能性。最后的最后,我还是我,可以是披荆斩棘的女战士,也可以是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公主。
找到自己不是终点,而是新的开始。唯有自己,不可辜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