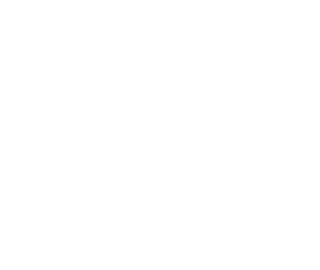树英成长2018 | 救赎迷茫的自己
救赎迷茫的自己
也许有人觉得华二的学生都是醉心于学习的学霸,其实不然。我也不过是一个有血有肉的18岁的学生,热爱自己的兴趣,渴望他人的肯定,时常迷茫、失落、甚至自我厌恶。如今想来,过去几年在树英教会我的最重要的,大抵就是怎样让自己认识与接受我之为人的每一部分,进而将其外显出来得以让他人欣赏吧。
我的整个申请季可以很贴切的用“置之死地而后生”来形容了。从去年12月19号芝加哥大学的当头一棒和接踵而来的EA各种reject和defer开始,我才切实地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普高的平凡学生在整个申请pool中显得如此渺小。浑浑噩噩了几天,在老板的鼓励下又心怀期望地把ED2的范德堡和RD轮的材料交了上去,迎来的却是更多的失望。整个二月和三月中的状态难以形容,也一度产生过对自己能力和留学意愿的怀疑。因为几乎没有收到什么offer,很长一段时间在申请群里没有和老师沟通。今年我所在的华二的美本申请录取情况总体上不算特别出彩,周围的同学都压力很大;然而我偏偏和两个巨神(一位ED2芝加哥,一位西北+WUSTL全奖)住同一间寝室,再加以老板朋友圈不断轰炸带来的树英小伙伴们peer pressure,一度导致我十分焦虑。所以在USC的portal上看到admitted student两个单词时感受到的先是惊讶,随后是难以抑制的狂喜,更有一种尘埃落定的安心感,或者说是归属感吧。正如老板一直所我说的“The best is yet to come.”,在最后关头被优秀的大学认同难免让人雀跃。现在想来这自始至终的种种表现和失态可能就是第一次到树英,跟老板聊天的时候他对我的评价“不够成熟”的体现吧——看来我还是以一个孩子投机的心态加入到申请季当中去的。
上周末从USC的admitted student session回来,感觉自己在不到13%录取率的今年申请季中拿到offer还是很幸运的。回想自己当时ED1芝加哥的选择,仅仅是基于其强大的经济系符合自己的兴趣和一次短暂的夏校经历,便感觉还是有些考虑欠妥。当然,我没有不喜欢芝加哥大学的理由,在那里体味到的卓越学术也不是空穴来风,但从那希望转变为失望的那一刻开始,我便不由得开始思考到底怎么样的大学才是适合我的。想起在芝加哥那篇稀奇古怪的补充文书,我选择的题目是“Tell us about your ‘armor’.”,大概意思是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中保持自我的盔甲。我写的是做一个孤独的行者,去探索感受身边事物的同时保持独立思考的经历,本以为已经很真实地表现自己了,却还是和芝加哥八字不合,大概在我这看似孤寂的内心中还是有些什么在燃烧着的吧。回头想来我大概也不是一个甘愿全身心投入学术的人——我记得当时在Essay班上,Kerri让我们用三个词描述自己,我第一个想到的词就是interest-driven。可以说自己是一个很贪玩的人了,学术以外,我在大学里还是有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建立别样共同体验的诉求的。如此想来,南加大那丰富的校园生活和强大的校友网对我来说不失为一种更有意义的体验。
此外,对自己专业的选择也有过很多纠结。自己的package里面有很多EALC的成分,对日本文化抱有的兴趣也丝毫不假,但求生本能告诉我只读一门文将来很可能没饭吃。记得母亲建议过去读数学,理由是本科读基础学科对深造和将来发展有利,但这种可以预想到的煎熬让我难以妥协。后来渐渐形成的想法还是读一门自己喜欢又富有实用性的经济,在此基础上再去考虑double major等等。说是感兴趣,其实也就是高中政治老师带进门,读《国富论》的时候产生了去了解更多的想法,也渐渐就开始了后续的阅读和研究。不过既然USC的专业那么多彩,还没下定决心的我到时候改变心意想来也不会是什么大问题吧,毕竟据USC招生官透露有一半左右的学生换过专业呢。总而言之,考虑专业时的理想和现实的权衡让我思考了很多,而美国大学能够灵活调换major的便利对我而言也是将来潜在的机遇。
我在树英的经历一定程度上让我克服了表述自己意见的障碍。也许是家庭和升入的高中的氛围使然,也许是受到自己本分克己的价值观念的影响,总之近年来愈发察觉自己对切实地向他人传达自身所想这件事感到时而烦躁,时而自卑。也明知这是不可取的,但这样的心病就是萦绕在身侧难以散去。然而在树英,表述自己的想法和展露自己的观点被塑造成了一种习惯。每一次workshop和那十天的Essay班给我带来的不仅是老师们的丰富经验,还有teamwork时身边的同学以自己的独到视角提出的建议和激烈讨论产生的火花,这些都让我受益匪浅。同时,在分析别人的作品时,我也渐渐对怎样表述自己才能更明了地被他人所理解和接受有了一些心得。还记得在essay班的日子过了一半,Kerri和Sarah开始要求我们着手主文书的写作了,我便拿出开班前已经和海外mentor商榷过五六稿的一篇文章来,本以为能在进度上先他人一步了,却直接被Kerri否了,理由是“不能像记流水账一样”。一开始写的是自己在高中创立日本文化社团的经历和主要成就,成文是三段式的记叙文,故事性着实不太强,也被告知了这样没有足够的吸引力。但说来惭愧,这种平凡无奇的瞬间无限地重合累积,大概就组成了我大部分的生活——于是我对Kerri坦诚相告,她也努力帮我出谋划策,很耐心地听我分析文中所写的每个部分想体现的内容。随后考虑下来,决定对创立社团的这段过程进行戏剧化的描写,反映出我在社会背景和他人的误解中坚持向身边的人诠释自己所喜爱的日本文化并得到理解的故事。成稿的那一刻,少有的感到了心中畅快,毕竟鲜有纯粹为自己落笔的经历,想来是内心感受在树英的老师们的引导下切实得到表达了吧。
树英教给我的另外一课是在正确认识自己的基础上将申请带来的压力化作动力,也是在这里,我才明白了申请不是力争上游,而是申请者和学校的两情相悦。首先是DTR不断在强调着的“fit”的概念,虽说很对不起树英老师们的教导,总感觉自己对部分申请的大学的了解还有些一知半解,想来这也是申请季前期失败的一部分原因。树英里优秀的小伙伴们强大的一面也不难从老板朋友圈的各式文章中窥探到,感受到的竞争力自然不小,但也对我有许多积极的影响。感谢这个团结而和谐的大家庭一直激励我在追求卓越的道路上走下去。
沸沸扬扬的申请季落下了帷幕,但眼前即将迎来的就是更加紧张刺激的美国大学生活。我应该会背负着这两年来的遗憾、喜悦和从树英这里学到的一切,向着救赎自己迷茫的内心迈出坚定的下一步吧。忽然想起东野圭吾的《解忧杂货店》里让我印象深刻的两句话可以很好的形容我的申请季:现在就是最后的时刻,我只要现在仍然坚信就好吗?那么就算打了一场败仗,我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了吧。
大家加油,fight on!~